劉飛的紅色家風(fēng)故事
大公無私、克己奉公、廉潔自律的劉飛將軍
劉飛,原名劉松卿,曾改名為劉松清、劉清,1905年12月31日出生于湖北黃安(今紅安)八里鎮(zhèn)羅家田灣,1927年任縣農(nóng)會主席,同年參加黃麻起義,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(nóng)紅軍,同年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革命戰(zhàn)爭年代,劉飛將軍身經(jīng)百戰(zhàn)、智勇兼?zhèn)洹④娬p全,曾6次負(fù)傷,是能征善戰(zhàn)、叱咤風(fēng)云的戰(zhàn)將,歷任山東野戰(zhàn)軍第一縱隊二旅旅長,華東野戰(zhàn)軍第一縱隊二師師長,第三野戰(zhàn)軍二十軍軍長。參加了淮海、渡江、上海等戰(zhàn)役。新中國成立后,劉飛將軍歷任皖南軍區(qū)司令員、安徽省軍區(qū)司令員、南京軍區(qū)公安軍司令員、上海警備區(qū)副司令員、南京軍區(qū)顧問。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街。以下故事主要由劉飛子女回憶組成。
“藥是重傷員的,不是給我兒子的!”
父親和母親一共生育有7個子女,老大是兒子,1941年生于皖南事變非常時期,取名劉非常。1944年,劉非常因患白喉夭折,這是他們心中永遠(yuǎn)的痛。晚年的母親對大哥的思念似乎格外強(qiáng)烈,每當(dāng)看到蹣跚學(xué)步的孩子,她總會喃喃自語,久久凝視……在之前我只知道哥哥患病夭折,直到我父親的老部下,鄭治叔叔給我講述我才知道當(dāng)年的情況:
當(dāng)年父親身邊有一個近三歲的兒子(就是我的非常哥哥),年齡雖小,但很懂事、很可愛,嘴也很甜。與媽媽在一起,從不煩人。小小年紀(jì)隨著部隊行軍是家常便飯,途中知道要乖乖的,克制自己不能暴露目標(biāo)。到了宿營地,還學(xué)戰(zhàn)士的模樣,跟著到老鄉(xiāng)家噓寒問暖,常逗得老鄉(xiāng)和戰(zhàn)士們哈哈大笑。戰(zhàn)士們訓(xùn)練時,他就會肩扛小樹枝,跟在隊伍后面,像模像樣地邁步子,學(xué)刺殺、臥倒等。當(dāng)時,他就是部隊干部戰(zhàn)士閑暇之余的開心果。父親更是對兒子痛愛有加。戰(zhàn)斗之余,父親只要見到兒子,總是先舉過頭頂,再用滿臉的胡須去扎扎那稚嫩的小臉,這是他們父子倆不變的見面禮。然后就是給兒子津津有味的講戰(zhàn)斗故事,有時還會教上幾句革命歌曲。只要有人問小家伙長大了想干什么?必定是挺起小胸脯有力的回答:跟爸爸一樣,打小日本!
誰知有一天孩子被傳染上了“白喉”病,治療及時,完全是可以治好的。但抗戰(zhàn)時期,部隊的藥物非常匱乏,也來之不易。就在軍醫(yī)準(zhǔn)備用“盤尼西林”(青霉素)為我哥哥治病時,被聞訊趕到的父親堅決地阻止了。父親非常嚴(yán)肅、堅定地說:這藥是給重傷員用的,我的孩子決不能用。這是命令!父親說話時兩眼濕潤了。誰都知道,如果不用“盤尼西林”,孩子就有生命危險。父親當(dāng)時也完全知道放棄治療的后果,就是意味著對他兒子生命的放棄。媽媽眼睜睜地看著抱在懷里唯一的孩子,經(jīng)過三天三夜的煎熬而痛苦的離開了人世。當(dāng)時在場的人都留下了眼淚。鄭叔叔說,你父親把戰(zhàn)士們的生命看的比自己唯一兒子的命要重,對我們的教育太大了,以至我們終身難忘。鄭叔叔在電話那端說著說著聲音哽咽了……
當(dāng)年父親身邊有一個近三歲的兒子(就是我的非常哥哥),年齡雖小,但很懂事、很可愛,嘴也很甜。與媽媽在一起,從不煩人。小小年紀(jì)隨著部隊行軍是家常便飯,途中知道要乖乖的,克制自己不能暴露目標(biāo)。到了宿營地,還學(xué)戰(zhàn)士的模樣,跟著到老鄉(xiāng)家噓寒問暖,常逗得老鄉(xiāng)和戰(zhàn)士們哈哈大笑。戰(zhàn)士們訓(xùn)練時,他就會肩扛小樹枝,跟在隊伍后面,像模像樣地邁步子,學(xué)刺殺、臥倒等。當(dāng)時,他就是部隊干部戰(zhàn)士閑暇之余的開心果。父親更是對兒子痛愛有加。戰(zhàn)斗之余,父親只要見到兒子,總是先舉過頭頂,再用滿臉的胡須去扎扎那稚嫩的小臉,這是他們父子倆不變的見面禮。然后就是給兒子津津有味的講戰(zhàn)斗故事,有時還會教上幾句革命歌曲。只要有人問小家伙長大了想干什么?必定是挺起小胸脯有力的回答:跟爸爸一樣,打小日本!
誰知有一天孩子被傳染上了“白喉”病,治療及時,完全是可以治好的。但抗戰(zhàn)時期,部隊的藥物非常匱乏,也來之不易。就在軍醫(yī)準(zhǔn)備用“盤尼西林”(青霉素)為我哥哥治病時,被聞訊趕到的父親堅決地阻止了。父親非常嚴(yán)肅、堅定地說:這藥是給重傷員用的,我的孩子決不能用。這是命令!父親說話時兩眼濕潤了。誰都知道,如果不用“盤尼西林”,孩子就有生命危險。父親當(dāng)時也完全知道放棄治療的后果,就是意味著對他兒子生命的放棄。媽媽眼睜睜地看著抱在懷里唯一的孩子,經(jīng)過三天三夜的煎熬而痛苦的離開了人世。當(dāng)時在場的人都留下了眼淚。鄭叔叔說,你父親把戰(zhàn)士們的生命看的比自己唯一兒子的命要重,對我們的教育太大了,以至我們終身難忘。鄭叔叔在電話那端說著說著聲音哽咽了……
知道這事后我向媽媽提起此事,媽媽出奇地平靜。她說:在那個年代,誰都會這樣做的。但是,孩子臨終前那無助和充滿期盼的眼神,是永遠(yuǎn)也無法忘記的。是啊,做為一個母親,在可以救而又不能去救自己的孩子時,內(nèi)心是多么痛苦!但她認(rèn)了,畢竟戰(zhàn)士的生命要比自己孩子的生命重要的多!我可親可敬的父親,我堅強(qiáng)慈祥的母親,你們在戰(zhàn)爭年代出生入死、前赴后繼、浴血奮戰(zhàn),為了革命的勝利,毫無保留得貢獻(xiàn)出了自己的一切!甚至自己孩子的生命!
言傳身教 去除“驕、嬌”氣
爸爸出生在貧苦農(nóng)民家庭,從小吃盡了千辛萬苦。參加革命后,在戰(zhàn)火紛飛的戰(zhàn)場上浴血奮戰(zhàn),英勇殺敵從未停息。解放后生活安定了,但他從未忘卻過去的一切,始終保持著工農(nóng)的樸實本色。我們家姐弟六人,三個姐姐從小就住讀子弟學(xué)校,培養(yǎng)了獨立生活的能力。1957年,我們家搬到繁華的大上海,環(huán)境變了,我們接觸的一切都變了,爸爸及時地教育我們要保持艱苦樸素,不要被燈紅酒綠的環(huán)境所迷惑。爸爸媽媽的襪子都是補(bǔ)了又補(bǔ)還在穿,內(nèi)衣更是補(bǔ)丁加補(bǔ)丁。我們兄弟三人從小都是穿著姐姐們穿過后改的衣服,鞋子都是媽媽自己做的,一直到上初中,也很難穿一件新衣裳。在學(xué)校我們穿著改小的軍衣,雖然鞋子和衣服基本都有補(bǔ)丁,而且是舊的,可我們感到很自豪。
我們兄弟三人上小學(xué)時,學(xué)校離家很遠(yuǎn)。每天一大早我們就迎著晨曦從淮海西路步行到靜安寺,中午在教工食堂蒸飯吃,下午放學(xué)又踏上歸途。無論是刮風(fēng)下雨,還是酷暑寒冬,從未間斷過。雖然爸爸就在靜安寺附近上班,可我們從來沒有“搭乘”過爸爸坐的汽車。爸爸媽媽看到我們這樣非常高興,夸我們能吃苦。爸爸還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講:“你們要記住,爸爸是農(nóng)民出生,參加革命前是碼頭工人,千萬不要像有些干部子弟那樣有‘驕、嬌’二氣。你們從小就能加強(qiáng)磨練,小小年紀(jì)走這么遠(yuǎn)的路是不容易,但這樣既能鍛煉身體又能克服嬌氣,真是一舉兩得呀!”
作為一名老黨員,父親的組織觀念極強(qiáng)。無論在艱苦的戰(zhàn)爭年代,還是和平時期身居高位,他都始終如一。“是黨員就是黨的人,應(yīng)要對黨忠誠老實。沒有組織觀念,就算不得共產(chǎn)黨員。”這是他時常教誨我們的話。記得有一次,我們兄弟三人難得從部隊回家團(tuán)聚,父母都很高興。晚上父母休息了,可我們談性正濃。突然父親身披棉襖闖進(jìn)門來,看著他嚴(yán)肅的面容我們楞住了。原來在交談中議論各自領(lǐng)導(dǎo)的話,被隔壁已經(jīng)就寢的父親聽見。他怒氣沖沖地大聲訓(xùn)斥我們:“你們算什么共產(chǎn)黨員,背后議論領(lǐng)導(dǎo)!他們代表一級組織,有意見到會上去提,這樣瞎議論,對工作對你們自己都沒有好處。”嚴(yán)厲的批評,使我們啞口無言。可心里還不太服氣,認(rèn)為是小題大做。這時父親又用自己的親身經(jīng)歷教育我們,他說:“我從抗大畢業(yè)后,同另外幾十名同志一起奉命調(diào)新四軍工作。臨行前,毛主席親自找我們談話。他說:‘你們都是師、團(tuán)干部,到了新四軍,只能擔(dān)任營、連級職務(wù),同志們要服從組織的安排,加強(qiáng)組織觀念,是共產(chǎn)黨員就不能計較個人得失……’我們照主席的教導(dǎo),在新的崗位上拼命工作,英勇作戰(zhàn)。后來,都成為新四軍的骨干。”從此,我們兄弟三人無論在什么崗位上,都能服從組織決定,不斷地增強(qiáng)自己的組織觀念。
“什么都不留下”
父親出生貧苦,小小年紀(jì)就擔(dān)負(fù)起家庭的重?fù)?dān)。三歲喪父,八歲給地主放牛、打短工,后到武漢當(dāng)茶役、當(dāng)碼頭工人。童年是在饑寒交迫中熬過來的。因此,他的吃苦耐勞性特強(qiáng)。解放后,他先后擔(dān)任過不少軍隊的高級領(lǐng)導(dǎo)職務(wù),可勞動人民的本色從未改變。他對吃穿從不講究,夏天最愛穿舊布條打的“草鞋”。一般人都不屑一顧的粗茶淡飯,吃在他嘴里總是香噴噴的。給父親做飯的炊事員都說:“我們首長的飯菜最好做,我燒什么他就吃什么。”勤儉節(jié)約是他的嗜好,我們誰要不注意隨手關(guān)燈,就免不了挨頓訓(xùn)。直到晚年,他行走不便時,每天晚上仍要樓上樓下的巡視一番,一個水龍頭一個水龍頭,一盞燈一盞燈地檢查。
父親總告誡我們說:“自己的路自己走,想靠父母是靠不住的。不要學(xué)那些沒出自的孩子,躺在父母的功勞簿上吃張口飯……”幫助我們克服盲目的優(yōu)越感,養(yǎng)成獨立性,各自去闖一條自己的生活道路。我們兄弟三人相繼應(yīng)征入伍在當(dāng)戰(zhàn)士的幾年里,大家都難得回家。父親也從未給我們寫過信,可是他對我們的教誨卻時常回響地我們耳旁。激勵我們努力工作。在我們?nèi)朦h,提升等問題上,他從不利用職權(quán)加以干涉,給我們的只有一句深沉的話:“各自好好干!”這一句再普通不過的話,蘊(yùn)涵著父親對我們的殷切期望。我們始終努力的工作學(xué)習(xí),在基層工作最短的也有十幾年。當(dāng)我們有調(diào)動機(jī)會時,父親從不為此去找關(guān)系,反而對我們說:“當(dāng)兵就要在基層鍛煉,想進(jìn)機(jī)關(guān)圖舒服是不會有長進(jìn)的。你們不要指望父母,要有出息就得靠自己去干,這才是真正的本事。”就這樣我們都一直在基層部隊工作了十七、八年,多次立功,二弟還被評為“南京軍區(qū)精神文明標(biāo)兵”。我們都成為各自單位的骨干。
父親的言行影響著我們,從小就培養(yǎng)成艱苦樸素、自力更生的好習(xí)慣。父親常說:“我是無產(chǎn)階級,一無所有,這洋房、汽車、家具統(tǒng)統(tǒng)是公家的,連我這個人都是黨的。我死后不會給你們留下什么遺產(chǎn)……”親愛的父親,您可知道,您給我們留下了是難忘的教誨,是奉獻(xiàn),是奮進(jìn),是追求。您給了我們“人之初”,給了我們智慧和力量。給了我們一生中的無價之寶——自力更生、廉潔樸實!
“我個人不算什么”
父親由于長期過度操勞,1964年3月底的一天,胃病發(fā)作,昏倒在會議室,被送往上海華東醫(yī)院搶救,經(jīng)檢查,患了胃癌。在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、南京軍區(qū)司令員許世友等的親自關(guān)懷下,當(dāng)即在華東醫(yī)院手術(shù),父親的胃被切除四分之三。由于醫(yī)護(hù)人員的精心醫(yī)治和母親的悉心照顧,父親終于闖過了這一關(guān)。病休期間,父親本想寫點回憶錄,但《沙家浜》一劇打消了他的想法。《沙家浜》是由滬劇《蘆蕩火種》改編而成的。父親既是《蘆蕩火種》的人物原型,又是該劇素材的最初提供者,也是該劇創(chuàng)作的熱情支持者。那是1939年9月,在江陰顧山戰(zhàn)斗時一顆子彈打進(jìn)父親的胸部,后他以堅韌不拔的毅力,忍受著傷病的折磨,率領(lǐng)36名傷病員和10余名醫(yī)務(wù)人員,在陽澄湖畔一邊養(yǎng)傷,一邊堅持斗爭,使這一帶的抗日武裝(簡稱“江抗”)日益發(fā)展壯大。
淮海戰(zhàn)役時,第二十軍的新華社隨軍記者、作家崔左夫?qū)Ω赣H進(jìn)行采訪,父親向其講述了上述江抗36個傷病員的戰(zhàn)斗片斷,并要崔左夫好好寫一寫這些事。崔左夫聽后十分感動,經(jīng)過進(jìn)一步采訪,于1957年寫成此稿,題為《血染著的姓名》,并以此稿作為“解放軍建軍30年征文”投發(fā)。1958年春,崔左夫的老戰(zhàn)友、上海滬劇團(tuán)副團(tuán)長陳榮蘭將此稿推薦給劇團(tuán)的編劇文牧,文牧遂將它改編為劇本《碧水紅旗》。當(dāng)他們得知劉飛就是36個傷病員的領(lǐng)導(dǎo)人時,便將劇本拿來征求我父親的意見。此時,父親的秘書高松和我母親剛剛完成由父親口述的36個傷病員戰(zhàn)斗生活回憶錄《火種》,父親便將《火種》文稿交給他們參考。陳榮蘭、文牧根據(jù)《火種》又對劇本進(jìn)行了修改,并更名為《蘆蕩火種》。父親還安排劇組到由江抗36個傷病員發(fā)展起的部隊體驗生活,進(jìn)行再創(chuàng)作。后來《蘆蕩火種》在上海公演,獲得社會公眾好評和良好反響。
1964年5月至7月間,《蘆蕩火種》在北京公演,受到毛澤東的好評,后將此劇移植為京劇《沙家浜》。《沙家浜》一時唱紅了全中國父親的本意是想宣揚(yáng)36個傷病員的革命精神,但熟知父親經(jīng)歷的人都拿劉飛當(dāng)劇中人物郭建光。父親是一個從不愿意張揚(yáng)和宣傳自己的人。從此以后,他決意不再寫有關(guān)他個人經(jīng)歷的回憶文章。后來,崔左夫多次請求給父親寫回憶錄,父親總是那句話:“我劉飛個人算不了什么。”崔左夫最終未成心愿。
1984年10月24日,父親在南京病逝。父親生前常對我們子女說:“我是無產(chǎn)階級,一無所有,房子、汽車、家具統(tǒng)統(tǒng)是公家的,連我人都是黨的,我死后不會給你們留下什么遺產(chǎn)。”父親遺體火化前,母親要求醫(yī)護(hù)人員取出埋在父親胸腔45年的彈頭,留作紀(jì)念,以激勵子女。我們把這枚彈頭視作父親留給我們的最珍貴遺產(chǎn)。這枚彈頭后被蘇州革命博物館收藏陳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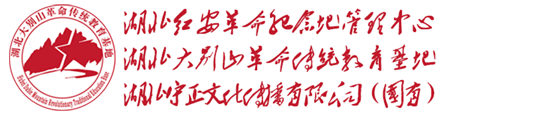
 打印本文
打印本文 關(guān)閉窗口
關(guān)閉窗口